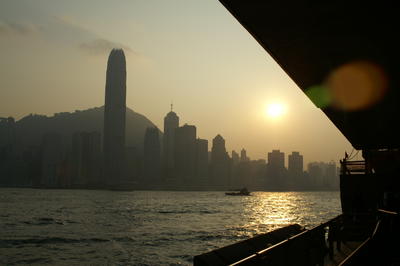貧富

才剛呻完開工不足,工作便立刻接踵而至。臨近月尾,資料搜集的工作忙得不可開交;圖書館辦了補課班,要求我去幫忙;也要趕及截稿的日子,除了自己的照片外,也要幫其他記者拍照。那個拍攝工作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。自己一向也不擅長拍攝體育照片,再加上是夜晚的關係,為工作加添了難度。現場是深水埗一個足球場,那裡的景象像在提醒人們,別忘了香港還有身處極低下階層的人。放眼所見,公園內都是一些目無焦點的伯伯,也有些印巴籍的婦孺,在納涼,也有不知在幹甚麼的。即使燈光昏暗,小孩子也照樣在嬉戲。為甚麼不回家呢?我家附近的公園過了晚飯時間便沒人來往,準是他們因環境問題,根本不想留在家中:或是太熱、或是有個醉酒的丈夫,總之,我剎那間覺得,貧富兩極化並不是一個遙遠的課題。
雖然現場有大光燈照明,但因為要拍攝的是一隊球隊的操練情況,不斷的活動使我不能將快門調得太慢,結果我需要用到最高的ISO1600才能勉強拍到。在初頭未習慣的情況下,我足足用了差不多十分鐘、拍了三十來張照片來適應。幸運的我生在數碼時代,可以跟著成品來調較曝光值。想起上次拍籃球賽,那是還未有DSLR,三筒菲林才能勉強選出數張構圖好、曝光正確的照片來。還好,最後也能完成任務,希望編輯收貨,使我辛苦拍來的相片有見光的機會吧。